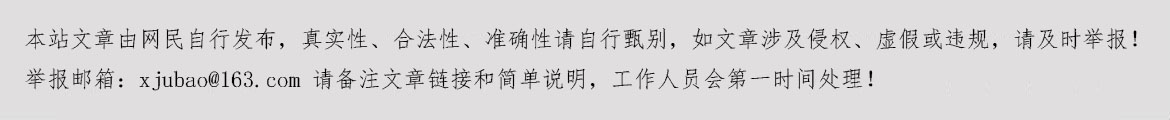安卓手游下载 http://www.xiaopin6.com
作者丨郭亨宇
佘璐芸觉得很多事情自己还没想清楚——对她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她觉得秉持某种不容置疑的概念生活着的年轻人是无聊的。
1 月 20 日下午三点半,佘璐芸一袭黑衣,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出现在北京望京街头。她长着一张臭脸,不说话时看起来像在生气。
这天,她要去参加一场试戏。这是一部学生作品,导演是一位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女生,也是佘璐芸的朋友。在这部作品里,佘璐芸扮演一位破产的中产阶级女人,不找工作,以变卖家具为生。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 1997 年出生于深圳的狮子座女孩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今年大三,是个小有成就的青年艺术家。
试戏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属于导演和男演员。佘璐芸盘腿坐在椅子上,咬着右边的一缕头发。除了搭戏,她基本不说话。觉得无聊了,就起身逗猫。猫的名字叫加州,黑白条纹,矫健漂亮。佘璐芸唤它的名字,把猫抓到怀里,猫跳走,她再抓回来,反复几次,她索性用小臂把猫紧紧搂住,腾出两只手捏猫的脸颊。
她觉得猫愿意窝在她怀里了,一松手,猫又蹿到了房间另一头。
或许是因为早早敲定了让她演女主角,这天下午,佘璐芸对试戏并不起劲。她的精力更多分散给了一个将在 1 月 23 日上线的线上展览。展览由拟像空间——一个位于北京的艺术家团体主办,佘璐芸是策展人之一。他们打算把展出的作品放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只给观展者抛出作品的文字介绍,观展者要找到隐藏在文字中的“关键词”,通过后台回复正确的“关键词”才能查看作品。
佘璐芸想尽可能把这个线上展览做得好玩,她想把关键字的设置和引导人们寻找关键字的过程,设计成一个能勾人玩下去的文字游戏,但设计了好几版,还是觉得这个游戏“笨笨的”。
设计游戏不太像佘璐芸该干的事。去年 10 月,她因为做了一个叫“当代艺术驱动器”的电子装置,成了班上唯一一个做了暑假作业的人;而通过卖“当代艺术驱动器”,她也成了班上率先达成“月入十万元成就”的人。
在这个“小有成就的青年艺术家”看来,艺术家不过是一份职业,没什么好清高的;她不喜欢“艺术家”这个词在一些语境下变成一种揶揄,成为艺术家也并不可耻。如果非要说一个生活的目的,那么她的目的就是打破人们对“艺术家”的幻想。
艺术家能赚大钱也不错
佘璐芸的“月入十万”来得猝不及防。
2020 年暑假,她回到深圳。导师没有留作业要求,她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就开始做白日梦,希望有一个有求必应的“小伙伴”源源不断地为她提供艺术创意。
最初,佘璐芸只希望能做几个机器帮自己想主意,但在和其他同学的聊天过程中,她意识到“没有主意”不是她一个人的烦恼。于是,她向经营电子加工厂的父母求助,问他们能不能帮她做这样一个装置,父母同意了。“当代艺术驱动器”的构想开始慢慢成形。
佘璐芸想自己撰写一份“创意清单”,但她不擅长文字——第一次高考时,佘璐芸的语文只考了 50 分,她形容自己上大学前的文字表达是“完全混乱的”——于是她开始翻看大量艺术类书籍,从展讯、艺术批评和微信公众号文章里摘取各种各样的“艺术套话”。阅读过程中,“当代艺术驱动器”的最终面目逐渐清晰。
佘璐芸清楚,这个装置并不能真正给艺术家提供点子,干脆赋予了它一种讽刺意义,用于解构当代的艺术阐释体系。
设计完成后,佘璐芸还得自己学编程。她问懂计算机的朋友,不同的功能要用什么代码实现,再自己一个一个敲。最后,她到工厂督工,看着电路板在流水线上打孔、上锡、加元件,变成一块完整的装置,她自己还给 100 多块装置导入了程序。
这是一款能随机生成 680000 条艺术阐释的电子装置。大小相当于一块电子表表盘,由一块电路板、一个长条状的显示器、一个开关和一个按钮组成。使用者每次摁下装置上不起眼的四方形按钮,装置就会自动从词库里组合出一句诸如“扩展无人问津的新闻”、“解释有权力的觉”这样意义不明的短语。这个四四方方的小东西很轻,拿在手里时,就像捧着一块饼干。为了方便携带,佘璐芸给电路板打了一个小孔,喜欢它的人可以穿上链子,挂在腰间、胸前,或者其他任何想挂的地方。
佘璐芸最初只打算做 100 个——这是加工厂流水线运作一次所能做的最少数量,说到底,它只是一份作业。但对她母亲而言,厂里做 100 个和做 400 个成本几乎等同。于是,第一批“当代艺术驱动器”就做了 400 个。佘璐芸一开始没打算怎么卖,“可能就送送朋友,有时参加集市带过去卖几个,我还觉得 400 个肯定太多了。”
收获了很多“当代艺术驱动器”的佘璐芸
回北京后,佘璐芸私下送了几个给朋友玩。她看着朋友们认真玩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有些意外。她说,之前在创作过程中想找人讨论,但很多人对这个作品没什么兴致:“我还觉得它不会太受欢迎。”
2020年 11 月初,佘璐芸参加了木木美术馆举办的野生青年艺术节。那天她带了几个“当代艺术驱动器”摆在现场作为展示。有人路过时,问了她一嘴“这个东西怎么卖”。佘璐芸愣了一下,算了一个刚好能覆盖掉成本的价格,告诉对方一个卖 128 块钱。
结果一天之内,她拿到了三百多张订单,把剩下的“当代艺术驱动器”全部卖完了。
“我特别激动,跟我妈说这东西卖得不错,让她再做 400 个,结果我妈也是牛逼,当时就让厂里生产了 2000 个,还加急寄到我手里。”那一个月,佘璐芸觉得自己就像个开淘宝店的,每天都有各种“来路不明”的人加她微信要买“当代艺术驱动器”,她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发货。
那一个月,她卖出了一千多个“驱动器”,收入超过十万元。
“我妈就说,你靠这个能养活自己,我们就不给你打生活费了,我当时说,‘好啊’,我以为她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后来就真的不给我打生活费了。”佘璐芸告诉全现在。
在集市上卖“当代艺术驱动器”的佘璐芸
“当代艺术驱动器”的反响超出预期太多。那之后,有人想约她做采访,有人想让她直播带货。佘璐芸拒掉了很多邀约,但碍于情面还是接了一些。一方面,她觉得艺术能赚钱不是坏事,因为自己“挺爱钱的”;但另一方面,她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没有更多精力去做新的作品。
那段时间,她的微信经常转发和“当代艺术驱动器”相关的内容。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师在学校里叫住了她,说了一句:“佘璐芸你可别飘了。”
佘璐芸瞬间惶恐起来,“当时我也没觉得自己飘了,但他那么一说,我就觉得我肯定是飘了,反思了好久。后来我又去找这个老师,他说,他其实就是随口说了一嘴。”
再后来,她变得不太喜欢谈论“当代艺术驱动器”,突如其来的畅销和在青年艺术家圈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名气就已经让她厌烦。她不想让“当代艺术驱动器”变成一种局限:“我不想以后人们聊到我就只有一个‘驱动器’,也不想就这样确定我今后做实验艺术的材料,其实,我也不想用固定的一种材料来做艺术。”
艺术家的童年并不十分美满
佘璐芸制作“当代艺术驱动器”的材料,是一种叫 PCB 板(印刷电路板)的工业原件。
在设计时,她刻意地没有给“当代艺术驱动器”加装外壳。电路板、元件和电池统统暴露在外,能看见,能被触摸。佘璐芸觉得,这样有一种来自“第二工业”(secondary industry,即加工业)的美感,有更重的“赛博”气息。
佘璐芸喜欢“2020 实际存在”有一种“低智能化”的美感
佘璐芸对“第二工业”的痴迷源于童年记忆。2009 年,小学六年级的她在父母开办的工厂里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当时,佘璐芸想要一台 90 块钱的滑板车。她去找妈妈要钱,希望借此向妈妈传达一个消息:“别的小朋友都有零花钱,但是我没有”。妈妈让佘璐芸自己打工挣钱,她打了一天工,拿到了 150 块钱的工资。
在小学到初中的前几年,佘璐芸放学后经常到电子加工厂等妈妈下班,需要零花钱就靠打工自己挣。当时的工厂自动化程度还不高,有很多活需要人力。小孩子视力好,手也稳,可以做很多往电路板上安置微小元件的活计。
工厂、流水线、电子元件这些元素,直到现在都影响着她的审美。
家里生意很忙,佘璐芸又是独生女,被散养的她比同龄人更早地获得了“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的自由。上初中后,她开始向爸妈要一点钱,报周末的画画培训班。
彼时佘璐芸开始展现出某种反叛的气息。当时女生流行剪“波波头”,她也尝试了一次,结果剪完后觉得自己“看起来很蠢”,就让理发师把头发再剪短一点,剪到露出耳朵。剪到最后,佘璐芸看起来就像个男生。
顶着男生头回到学校,一位女同学悄悄问她:“你是不是 T?”佘璐芸回应以“轻蔑的一笑”,不置可否,转头上网搜索“什么是 T”,才知道那是女同性恋的一种称谓。
她知道自己喜欢女生,只是不知道“T”代表什么。“大概在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女生。”佘璐芸回忆,“直到一天有个女生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不用解释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也突然知道喜欢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最初她因为这件事情哭过,觉得自己不正常。直到网络上开始出现“腐女”这个群体,借由各类网络文学,同性恋群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妖魔化,佘璐芸才“弯”得安心了一点。她变得咋咋呼呼,自由散漫,还经常在初中生上演“热血高校”的打群架戏码时被叫去撑场子。
就这样一直晃荡到中考临近,她才发现以自己的成绩上不了任何一家深圳的公立高中。考前,佘璐芸被老师叫过去骂了一顿,老师说:“你能不能不要参加中考,拖低我们学校的平均分,你不是会画画吗?不是有什么美院附中那样的(艺术类高中),你去考那些学校。”
抱着“考一下试试”的心态,佘璐芸考上了一家四年制的艺术类高中。
上高中后,佘璐芸觉得有点没意思了。她告诉全现在:“深圳的艺术高中其实是比较业余的学校,除了教你画画,不会给你传授一些艺术史之类的知识。”
那段日子,佘璐芸的父母开始闹离婚。在婚姻中得不到回应的母亲变得十分依赖佘璐芸,经常不分时段地给她打电话倾诉,很多事情都要她帮着做。离婚牵涉到财产转移,佘璐芸最忙碌的时候一天跑了无数趟银行,并为此办了十几张银行卡。
最后她实在顾不过来,索性给父母找了个律师,让他们离婚,“但最后他们也没离。”
家庭的琐事就像驱不散的乌云,佘璐芸只能用“更认真地画画”抵御烦躁。她开始萌生逃离家的念头,在高二的某个假期,她来北京追星,顺便找了个画室,打算完成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
在画室,佘璐芸发现有不少艺考生都以“央美”为目标。当时画室有一个专门为艺考应届生准备的重点班,佘璐芸就冒充应届生混了进去。因为画画水平还可以,老师也没有识破她。
2017 年,佘璐芸第一次高考因为文化课分数不够,没能考上。她准备复读一年继续考。结果第二年,一个已经考上美院的女朋友找她倾诉,她才发现美院远没有想象中的有意思。
“当时我知道了,即使你上了美院,做的东西还是没有改变,依然要去‘抄调子’。”佘璐芸说。“抄调子”是艺术生圈的“行话”,指在素描的时候,看见什么东西就如实地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在纸上重现。艺考前,老师会反复强调不要“抄调子”,这是艺考中被视为下乘的做法,意味着画画者对事物本身的理解仅停留于表面,没有按自己的理解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加工。
“但实际上,学再多画画的技巧和观察的方法,最终也只是学会了更高级地去抄调子。因为事物事实上就是这样子。”佘璐芸意识到,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后续的人生可能永远都在干这一件事情——就是画画,“抄”客观事物的“样子”。
她不想考大学了。
她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2017 年,佘璐芸去了一趟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国卡塞尔,看了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览,接触到了实验艺术。“一切东西都太牛了,直接冲击了我”,她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东西,接下来的一年,佘璐芸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
艺术家更多地凭借直觉
进入大学后,佘璐芸大部分时间花在作品上,不像其他同学总有那么多彷徨。
她将其归功于自己缓慢的成长速度:“我从小到大经常留级,小学四年级留级、初中二年级留级、高中留级,所以我跟现在的同学最大的不一样是我年纪很大,而他们可能还在过青春期。我就比较踏实。”
踏实并不意味着墨守陈规。上大学后她和另外两个女生组了一支叫“淡水兔”的乐队,学会了纹身,大一至今所创作的作品更是充满讽刺意味。
例如用马克笔在一尊大卫的石膏头像上,点上各种在中国传统面相学中被视为坏预兆的痣,配上“大卫你现在无法战胜歌利亚”的阐释;例如把咖啡豆、女性性玩具和光盘封进石蜡里,做成假书籍,讽刺书籍在成为消费品后,拥有大量书籍给人带来“富有知识”的虚幻感;例如因为自己对艺术市场的怀疑而拍摄的一段与“逃离”有关的影像。这些作品甚至有一部分是她随手促成的——有时担心作业不过,她会凭借直觉做几个没有过多考虑的作品,结果这些作品反而得到了老师的褒奖。
有一次,佘璐芸的“淡水兔”乐队在酒吧表演的时,和一位陈姓顾客起了争执。
小陈不满“淡水兔”乐队的歌没有歌词,直言佘璐芸这些艺术学院的学生“占着茅坑不拉屎,形式大于一切”,他认为摇滚乐的关键在于有所表达。佘璐芸不爽,她在另一个晚上找了十来个人去酒吧里围着“小陈”问了 100 多个与“表达”有关的问题,并把过程录下来,变成了一段“探讨表达”的影像。
最后他们和小陈和解,小陈请了在场所有人一杯 shot,这段影像也成了佘璐芸的作品之一。
佘璐芸不爱谈论宏大的、概念化的大词,不爱用喊话的姿态做激烈的表达,觉得“解构”已经被用烂了。但与此同时,她的作品又是叛逆的,这种叛逆更多通过怀疑来表达——对既定规则、对时代、对习以为常的概念,甚至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她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佘璐芸觉得很多事情自己还没想清楚——对她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她觉得秉持某种不容置疑地概念生活着的年轻人是无聊的。
2021 年 1 月 13 日下午,佘璐芸又一次做了一个“凭借直觉”的决定:她要去剪个头发。
她最近正在过昼夜颠倒的混乱生活。当天下午,她有一个简短的会议要参加——青年文化媒体“BIE 别的”邀请佘璐芸参加 2021 年 1 月 24 日在武汉举办的线下集会,届时她将带着她的新作品:“2020 实际存在”前往集会,在那里展出、贩卖。
参会之后,她溜达到了三里屯,被一家美发店的推销员拦下。推销员跟她聊了一些与形象有关的事儿,说她的头发该打理了。佘璐芸觉得挺有道理,跟着去了。
她已经有一年没剪头发,之前烫的羊毛卷不加打理退化成了大波浪,染黄的部分褪到发尾。“确实该考虑一下漂亮的事”,她说,“我已经很久没想过好不好看这件事了。”
洗头的时候,她拿着手机拍了张头发沾满白色泡沫的自拍,发了条微博。那几天,她发微博的频率很高,因为困扰她的事情很多,发微博是一种微型的宣泄。
最困扰她的,是新作品“2020 实际存在”。这是一个和“当代艺术驱动器”不太一样的装置,收录了 2020 年 366 天里发生的 366 件事。机器打开后,使用者每按一下按钮,机器就会按时间顺序跳出一个事件,从 1 月 1 日开始到 12 月 31 日结束。最后,机器会提出一个问题:“你确定 2020 实际存在吗?”如果使用者选择确定,机器会开始自我销毁,变成一块废铁。
“2020 实际存在”的电路板设计图,外形是一个问号
想做“2020 实际存在”的念头来自于 11 月她参加的一堂诗歌课。对于 2020 这一年,她想做点什么,但一直没想好该怎么做。直到诗歌课上,她误打误撞写了一首题为《2020 实际存在》的诗,这个想法才慢慢在她脑子里长起来。
推进工作没有想象中顺利。当时, 366 个事件已经定下来,但具体到每个事件,她不想用板正的新闻标题形式去阐述,同时,她也想在社会新闻和一些不那么公共的个人事件中找到平衡——全部都是新闻事件,会失去对具体个体境遇的关怀。整体性也是个问题,事件的编排需要节奏感,这关乎事件前后的关联和事件带来的情绪。说到底,“2020 实际存在”还是一件装置艺术,艺术性不能为表达让路。困扰多了,她甚至开始怀疑这块装置能否回应“2020 是否实际存在”这个问题。
受其他文创日历的启发,佘璐芸在每个事件前会加入一个“宜某事”或“忌某事”的词条。1 月 13 日这天,她原本应该把全部词条完成,但洗头的时候,还有半年长的词条是空白。她知道再拖延下去将赶不上活动,决定在当天一鼓作气把词条解决掉。
艺术家也需要赶DDL
入夜后,佘璐芸要去朋友家吃晚饭。最近她刚搬完家,新家的洗手间坏了,她没法上厕所也没法洗澡,只能四处游荡投靠不同的朋友。
等朋友做饭的间隙,佘璐芸掏出电脑写词条。她做了一个石墨表格,除了“注意事项”一栏,大部分已经填满。给每个事件配上“宜 XX”或“忌 XX”已经不新鲜,她想做些不一样的,“注意事项”是一种能引起共鸣的对事件的反应,又不能过于直接。她一边写,一边抓头发、皱眉、摇头,高亮的光标在屏幕上一格一格往下跳,跳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庆祝‘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条目上,佘璐芸停留了片刻,敲下了“忌两面三刀”五个字。想了想,又把“忌”改成“宜”。
写了一会,她把白色毛线帽拉到遮住整个脸,平躺在不太干净的地毯上,等灵感自己冒出来。
吃完晚饭已经近十一点。佘璐芸还要和朋友去 KTV 唱歌,她要在 KTV 包厢里完成 6 个月词条的撰写。她说她有多动症,当周遭变得很吵闹时反而更能让她专注。她的朋友告诉全现在,这种事佘璐芸没少干过,一次他们去酒吧玩,朋友在蹦迪时她在边上看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书。
出发前,佘璐芸大声宣布:“今晚不准摇滚,不准民谣,今晚是华语乐坛专场,我要从华语乐坛汲取灵感。”进入包厢后,佘璐芸很快摆好了创作架势。起先她还会边唱边写:双手握着麦克风,唱到歌词触发她创作灵感时就赶紧坐下,腾出一只手飞快地敲击键盘,然后继续唱。后来,她索性窝在沙发上,麦克风抵在下巴,专心写词条,遇到会唱的歌哼哼几句。偶尔想不起想要的词,捏起拳头轻轻捶打键盘。
这两小时可能是佘璐芸近来创作最顺利的时候,光标最终跳到了 2020 的最后一天。她让朋友点一首五月天的《干杯》,边听边想。大概半首歌过去,她突然在屏幕上快速敲下“宜退步”三个字,对着麦克风大喊一声“搞完啦”,发泄地把帽子摔在地上,推开电脑,认真唱完了《干杯》。
当晚的工作完成了。佘璐芸给导师发完文件,整个人垮在沙发上,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后续的日子依然被琐碎的忙碌填充。1 月 20 日晚上,距离去武汉不到 48 小时,佘璐芸试完戏回到家做最后的准备,等待工程师回复“2020 实际存在”的开发进展。在北京朝阳区的一间复式里,佘璐芸独享着唯一一间面积不到 20 平方米的隔断间,装满创作材料的箱子分散堆积在房间外的过道、阳台和厨房。一台 PS4 游戏机压在电脑音箱底下,混在创作材料中的手柄积起了一层灰,太久没碰的 Switch 电量用尽,安静地躺在床头柜里。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工程师才打来电话,告诉她原先设定好的文本内容因为长度和格式问题无法在机器上正常显示,需要马上修改。佘璐芸慌了神,原本她已经算好时间,卡着点刚好能在 demo 版机器出来的时候赶上集会。
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佘璐芸只能一条条校对修改。两小时内,佘璐芸蹲在椅子上抽着烟,把 366 条文本格式改好,编辑其中过长的词条,再重新发给工程师。
佘璐芸在工作中,左侧的日程版已经有一个月没更新了/图片来源:全现在
赶完工已经过了零点,佘璐芸坐在地上放松,思考要不要给自己点个外卖。
她总能让自己感到自在。佘璐芸似乎在践行“想干嘛就干嘛”的信条,生活中充满了“临时起意”。突然兴起一个人租车到雪场滑雪,约好采访后被推销员打动去剪头发——一个个撒野的片段像一张张切片,构成了她的生活。
当被问起对艺术家的看法时,佘璐芸记起老师曾教授过她:“艺术家要学会造自己的人设,要控制采访你的人”,但她不在乎。至于不在乎的理由,从她的认知里能搜索出很多答案,或许是解构主义对她的影响,她觉得那种“把一切不负责任地抛向空中”的态度“狂欢且帅气”;或许是对秩序的反抗,也或许是对“权威”姿态本能的怀疑。但当时,她给出了最简单的一个:
“因为我还年轻。”
(如无注明,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